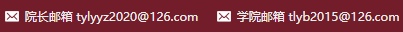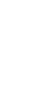警钟长鸣
人事代谢、古往今来之间,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一直流淌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历史向未来的呼唤既有丰富的智慧,也有深刻的经验。几千年间不断沉淀出深厚的监察法律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中华监察立法经验,在世界历史范围引人注目。
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现了治官之法,并孕育了职官监察法的萌芽。及至春秋战国,社会关系重构,封建官僚制度逐渐取代世卿制度,“治吏”成为权力监督及立法重要内容,职官监察法开始向成文法过渡。秦朝大一统之后,监察御史系统初步建立,监察法逐渐独立于官刑体制之外。汉承秦制,监察系统走向独立,监察体制多元化发展,监察法制最终形成。汉惠帝刺察三辅的九条,是性质较为明确的监察法规,到汉武帝《六条问事》,全国性的地方监察法规就产生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台建制更加规范,监察权不断扩大,监察立法在社会变动中仍保持活跃态势,产生了曹魏《察吏六条》、西魏《六条诏书》、北周《诏制九条》等代表性监察立法。唐朝建立一台三院,形成谏官系统,封建监察体制开始定型,监察立法也得到很大发展。官方制定的《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为监察提供了大纲大法,皇帝颁发的诏令是监察法的重要内容,以玄宗《监察六条》为代表的专门监察法达到新的历史水平,这些构成了唐代监察立法严密的制度笼子。
宋代将监察官作为朝廷的“耳目之司”,对监察权的控制越来越严格。有宋一朝监察立法的典型特点是以敕令为主要形式,并制定了《监司互察法》,加强对监察权的监督制约,旨在防止“灯下黑”。元朝的监察法制整体粗放,而且立法与司法严重脱节,但是制定了专门性的监察法,其中《宪台格例》作为监察法总则,《行台条画》则属于分则,在立法技术上属开创之举。
明朝设立都察院将监察权统一,直接对朝廷负责,为“肃纲纪、清吏治”,监察立法规模化、严密化,取得了重要成就。明太祖亲自删定的《宪纲》四十条,是明朝最早、最重要的监察法,之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法规。明英宗制定的《宪纲条例》,成为其后历朝监察立法的蓝本。同时,《监官遵守六款》等监察“工作规则”也不断完善。清朝监察立法形成了特有的结构形式和相对独立的体系。乾隆朝编纂的《钦定台规》,经嘉庆、道光、光绪历次修订,合称“四朝台规”,是封建社会监察立法的最终完备形态。
纵观历代监察立法,大致实施方式有以下几点。
一是逐渐走向专门化和法典化。鉴于权力监督运行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历代都十分注重监察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从前面对发展脉络的简单勾勒不难看出,古代监察法从形成发展到成熟定型是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这也是封建社会权力运行监督体制不断走向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运行的反映。从零散的带有监察法性质的诏、令,到《六条问事》等地方专门监察法规,再到隋唐《司隶六条》《监察六法》等专门化监察法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是从分裂到统一、增强权力及对权力监督有效性的需要。清代因袭明代《宪纲条例》并结合国情创定的《钦定台规》,诞生于古代封建社会最成熟时期,历六朝一百余年,四次修订,是历代监察法规之集大成,是封建社会最后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监察法典。
二是典型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征。受制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古代监察法规要做到“历世遵其道不变”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制度变迁的非预期性,顶层设计得跟着实践发展走。这些监察立法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平衡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但是不同时期具体任务又有所不同。在中央权力并不稳固的封建社会前期,侧重的是地方监察法规的制定。例如,汉代《六条问事》是强干弱枝政策的产物,侧重约束地方权力,强化中央权威,其主要监察对象是强宗豪右、二千石高官等“关键少数”,针对性十分明显。在中央集权得到强化之后,对国家官吏队伍的监督制约成为监察法的重点内容。唐朝《监察六条》产生于四百年分裂割据再次统一、地主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所以将地方牧宰作为监察重点,世家大族反而成了监察之末。明朝的监察立法重心多在巡按御史出巡立法,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强化。
三是监察权不能任性。中国古代监察官位卑权重,是治官之官、纲纪所系,汉代的刺史、清代的巡抚等很多监察官职最后都演变成了地方首牧,所以历代对监察官的选任使用都十分重视。为防止监察官擅权专横、失职渎职,在监察立法实践中对监察官的监督制约也高度重视。宋朝监察法就系统规范了监察官的法律责任,推行各层次的互察法,监察官可以弹劾百官,百官也能监督监察官,监察官相互监察,监司相互监督,将监察权放置在“无影灯”之下。有明一代,都察院法规、六科监察法规、出巡监察法规都逐渐完备,对监察官的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程序严密、措施具体,对形成过硬的监察官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廷飞)